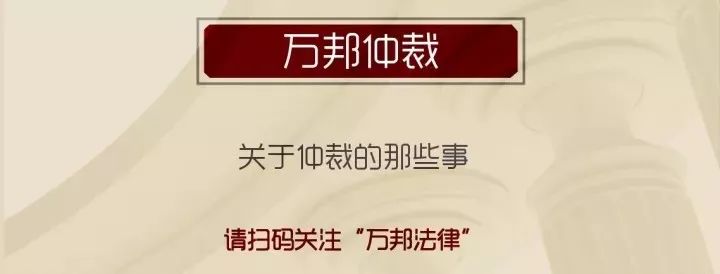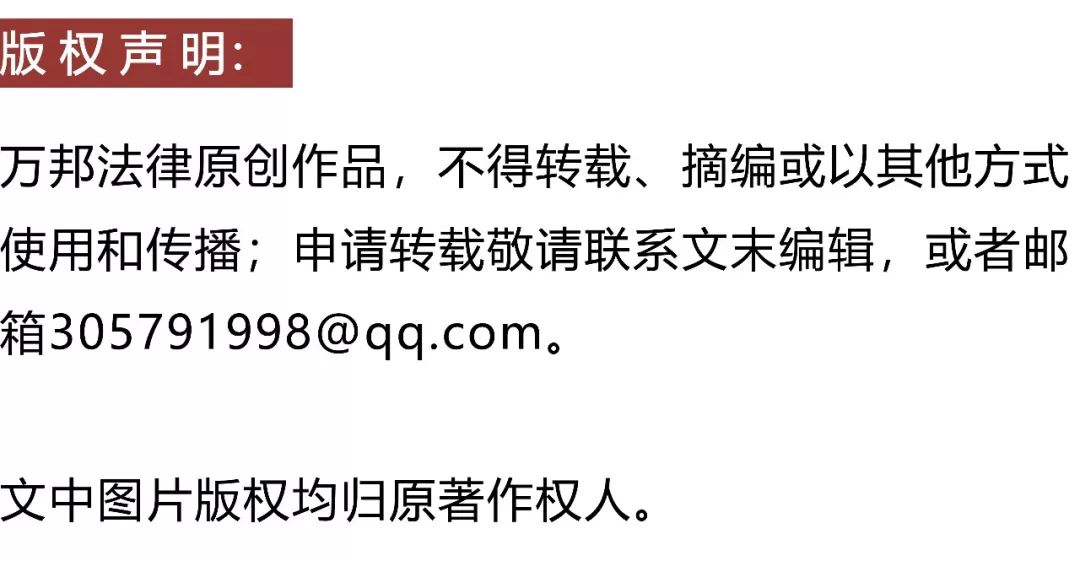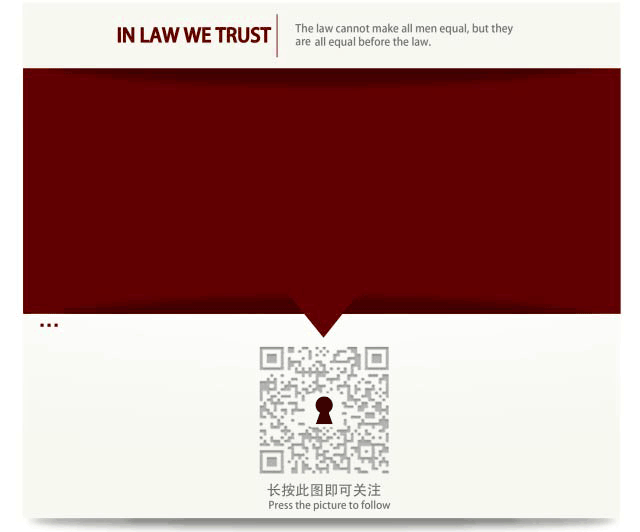萬邦法律
公衆號ID:wonbangl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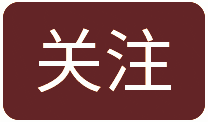
全文共7437字,閱讀大約需要42分鍾
本文首發于萬邦法®律
導語
2019年7月1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就一起涉及中國的仲裁案件作出判決,駁回原告仲裁管轄權異議的同時,認可了三個中國主體之間將無涉外因素案件提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的協議效力。本案在國內引發了較大爭議,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法院在協議明確約定在上海仲裁的情況下,仍認定新加坡爲仲裁地,並適用了新加坡的法律判斷該仲裁協議效力,由此引發了可能造成裁決不確定性、對協議解釋是否過度“仲裁友好”等方面的質疑。在判決中,新加坡法院比較詳細地探討了與仲裁協議法律適用有關的諸多問題,除了引發爭議的仲裁地認定外,還包括仲裁協議准據法的確定、仲裁協議獨立性的影響以及對有效性原則的理解與適用等。據悉,該案件仍可以上訴,但無論該判決是否最終被上級法院維持,其所涉及的問題都有不少研究的價值。
案例索引
BNA v. BNB and another [2019] SGHC 142
案情簡介
本案爭議産生于原告和第一被告于2012年簽署的一份長期資助協議(Takeout Agreement,以下稱原合同),在2013年,原告又與兩被告簽訂了一份補充協議,對原合同進行了一些修訂,第二被告作爲主債務人加入其中,第一被告成爲了承擔連帶責任的當事人。原合同第14條規定了爭議解決方式,其中第1款約定本協議適用中國法,第2款則約定如雙方發生爭議且未能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則提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在上海進行仲裁,並適用該中心規則。新加坡高等法院認爲,該條約定不但適用于原合同,也適用于補充協議。
2016年,兩被告發出仲裁通知,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啓動了本案的仲裁程序,原告隨即提出管轄權異議。本案仲裁庭成員均由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指定,新加坡律師許廷芳律師作爲首席仲裁員,楊良宜先生和鄭若骅女士爲邊裁。經雙方對管轄權發表書面意見,仲裁庭多數意見駁回了管轄異議,認爲本案仲裁協議應適用新加坡法,中國法與本案無關,故仲裁協議有效。而鄭若骅女士提供的少數意見則認爲本案應適用中國法且不具有涉外因素,而中國法律禁止將沒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故仲裁庭沒有管轄權。
其後,原告根據新加坡國際仲裁法第10條第3款的規定,請求新加坡法院判斷仲裁庭對案件是否具有管轄權。
爭議焦點
雙方當事人的意見針鋒相對,原告極力主張仲裁協議的准據法(proper law)應當是中國法,兩被告則認爲應適用新加坡法。對此,新加坡法院總結出四個爭議焦點:1仲裁協議的准據法是哪國法;2.本案的仲裁地是哪裏;3.在確定仲裁協議准據法時,主合同准據法和仲裁地法之間存在怎樣的相互影響;4.如果本案適用的是中國法,仲裁協議是否有效。
一、確定仲裁協議准據法的基本原則
通過總結英國的Sulamérica案(Sulamè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v Enesa Engenharia SA [2012] EWCA Civ 638)、新加坡高院的BCY案(BCY v BCZ [2016] SGHC 249)和BMO案(BMO v BMP [2017] SGHC 127)的裁判意見,法官歸納出判斷仲裁協議准據法的六項原則,包括:
1.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與其他合同的法律適用在方法上是一樣的,即法院應認可當事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意思標准。如果缺乏這樣的意思表示,則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准據法。這也是英國法院在Sulamérica案中采取的方式。
2.判斷准據法的三階段法包括:(1)當事人是否有明確約定仲裁協議准據法;(2)當事人是否有默示約定仲裁協議准據法;(3)與仲裁協議具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
3.三個階段應的判斷當分別並且按照順序進行;
4.在判斷仲裁協議准據法時,仲裁協議的獨立性應當被考慮;
5.仲裁協議獨立性意味著仲裁協議的准據法並不一定和主合同的准據法一致。即使如此,獨立性原則並不意味著仲裁協議和主合同完全割裂,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仲裁協議的准據法,而爲主合同選擇了准據法,在沒有相反證明的情況下,主合同的准據法可以作爲三階段判斷法中第二階段的重要指引(indication);
6.第二階段的指引可能來自合同條款的內容,也有可能來自被選定的主合同准據法可能使得仲裁協議無效這一事實。(判決第17節)
因此,對于法官而言,三階段判斷法是新加坡乃至于整個普通法系中判斷仲裁協議准據法的主要方法。法官同時指出,中國法律在仲裁協議法律適用問題上和三階段做法有很多相似之處,例如都是探討當事人明示或者模式選定的法律。區別在于,在當事人沒有明確或者模式選擇仲裁協議准據法的情況下,中國法會適用仲裁地法律,而新加坡則采取了多重因素分析法作爲三階段判斷法的最後一個階段(判決第20節)。
解釋仲裁協議的基本原則
隨後,法院回顧了新加坡上訴法院在2009年浙大網新案(Insigma Technology Co Ltd v Alstom Technology Ltd [2009] 3 SLR(R) 936)的意見,總結出在解釋仲裁協議時法院要遵守的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解釋仲裁協議的方法與解釋其他合同一致,即要認可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客觀表現出來的真實意思(判決第23節)。
第二個原則是如果當事人表明其願意將爭議提交仲裁,法院應當認可。這個原則又可以分爲兩個小點,一是法院不能過于限縮或者嚴苛地解釋仲裁協議,二是法院應當采取商業的解釋思維(判決第25節)。
第三個原則是即使仲裁協議中存在瑕疵,但只要瑕疵不是根本性的或者無可挽回的,達到足以否定當事人仲裁意圖地步的,就不會使得仲裁協議徹底無效(判決第26節)。
簡而言之,解釋包括仲裁協議在內的一切合同的最終的目的,都是通過解釋其文本探尋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而非打敗其真實意思(判決第27節)。
三、四個初步問題
進入三階段分析之前,法官還處理了四個初步問題,實際上是回應了當事人提出的幾個獨立于主要問題的主張。
第一個問題是被告提出提交合同起草過程中的草案作爲證據,但被法官以英美法系中的“書面證據”原則爲由拒絕。法官同時認爲,本案的合同足夠清晰,不需要再考察合同簽訂時的其他證據。值得注意的是,法官援引了當事人提供的中國法專家證人的意見,指出即使在中國法下,解釋合同也不需要考慮合同簽訂時的一切情形(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5條提供的合同解釋依據中並不包含這種情形)(判決第41至44節)。
第二個問題是被告提出的“有效性解釋”原則,該原則被總結爲當合同存在兩種解釋時,應當采取有利于協議有效的解釋。對此,法官認爲,盡管該原則與前述浙大網新案的第二原則類似,但仍有區別。區別在于兩點,一是有效性解釋的前提是合同必須存在兩種以上的解釋,而浙大網新案中的第二項原則並不存在這種情形。第二點更爲關鍵,有效性解釋的目的是赤裸裸地保證仲裁協議有效 (nakedly instrumental objective of ensuring that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effective),而浙大網新案的原則則是認可當事人關于爭議如何解決的真實意圖(判決第48節)。
第三個問題是被告提出的“有效性”原則,與前一個不同的是,有效性原則著眼于准據法的確定(法律適用)而非合同內容的解釋,即選擇有利于仲裁協議有效的法律。法官承認,雖然該原則是一個普遍被承認的國際性原則,但並不適用于新加坡,主要理由與第二個問題的類似,即新加坡法中的法律適用目的是爲了探尋當事人真實意圖,而非簡單地使仲裁協議有效。此外,法官同時指出,有效性原則在新加坡法律中並無存在必要,並且認爲該原則會給未來的裁決執行帶來問題(判決第65節)。
第四個問題則是仲裁協議獨立性問題。法院指出,在英國,由于英國仲裁法第7條的明確規定,仲裁協議獨立性限于仲裁協議不因主合同的效力受影響而無效,適用的前提是主合同無效(判決第70節)。但在新加坡(該國成文法中沒有關于仲裁協議獨立性的規定),根據此前的BCY案等案例,仲裁協議獨立性可以由更寬泛的解釋,甚至可以用于挽救有瑕疵的仲裁協議(判決第76節)。
四、三階段判斷仲裁協議准據法
1第一階段——沒有明示選擇法律
原合同第14條第1款雖然選定了適用的法律,但爭議解決條款卻在第2款,法官認爲當事人沒有就仲裁協議明確選擇法律,即第14條第1款的法律適用條款只能確定主合同准據法。
2第二階段——以中國法爲起點,以新加坡法爲終點
在當事人沒有明確約定仲裁協議准據法的情況下,法院試圖通過第二階段判斷,尋找當事人默示約定的准據法。根據Sulamérica案和BCY案所確定的原則,主合同准據法會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指引。而在本案中,主合同約定的准據法爲中國法。法院遂同意以中國法爲起點確定適用的法律。
原告同意主合同准據法雖然在理論上可能被其他法律替代,但在本案中卻無可替代,理由有兩點,一是本案的仲裁地同樣是中國,二是即便本案仲裁地是新加坡,根據BCY案確定的原則,仲裁地法也很難替代主合同准據法成爲適用的法律。
對于仲裁地問題,新加坡法院作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論斷,即本案的仲裁地是新加坡而非上海:當事人約定在上海仲裁的同時,也約定了適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而根據當時有效的規則(2013年版)第18條第1款,當事人在沒有約定仲裁地的情況下,以新加坡作爲默認的仲裁地,故本案存在“兩個仲裁地”(第104節)。在此基礎上,法院進一步指出,鑒于一個仲裁協議不能同時存在兩個仲裁地,並且從雙方的約定中無法看出約定在上海仲裁可以被解釋爲以中國爲仲裁地,故法官認爲上海屬于開庭地(Venue)而非仲裁地(Seat)(第109節)。緊接著,似乎是爲了加強上述論斷,法官又進一步強調了上海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而非法域(第110節)。
對于仲裁地法律能否替代主合同准據法問題。法官指出,三階段判斷法的終極目的是認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而BCY案和Sulamérica案已經明確,如果仲裁協議根據主合同准據法無效,則可以不予適用(第115節)。而本案仲裁協議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非涉外因素案件提交境外仲裁,另一個則是敬挽仲裁機構在中國境內仲裁。根據當事人的專家意見,法院指出這兩個問題在中國法下是“不確定、充滿困難且變化迅速的”(uncertain, fraught with difficulty and rapidly evolving),而以一個外國法官的眼光通過翻譯件來了解則更增加了難度。因此,法官決定采取比較保守的看法,同意申請人關于本案協議根據中國法應無效的主張(第116節)。因此法官最終決定適用能夠使仲裁協議有效的法律,即新加坡法。
3第三階段——最密切聯系地法
鑒于已經通過第二階段確定了准據法,法官認爲沒有必要再判斷第三階段。但他同時認爲,如果需要判斷,他會以新加坡作爲最密切聯系地,因爲雙方選定了新加坡法作爲准據法。
案件評析
最終,新加坡法官根據新加坡的法律,作出了有利于仲裁的判斷意見。但與此前的支持仲裁判決不同,本案引發了極大爭議,主要在于法官在大綠適用過程中存在不少可商榷之處。
首先,該案法官對合同的解釋相當牽強。BNA案認爲選擇上海作爲仲裁地不等于選擇中國作爲仲裁地,這與一般的商業慣例及以往的相關判例均不符。仲裁實踐中,除非當事人有另外的約定,否則約定在某地仲裁,即可以視爲以該地爲仲裁地。在本案中,上海作爲中國的一部分,理所當然適用中國法(一如約定在倫敦當然適用英國法),足以排除適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中關于以新加坡作爲仲裁地的兜底規定。此外,當事人的合同內容非常明確,並未上海僅僅定位爲“開庭地點”,而法官僅僅因爲當事人沒有明確約定“中國”二字就認定上海不是仲裁地,顯然有失輕率。有評論者指出,新加坡高等法院這一邏輯不但勉強,而且會對將來的案件産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其次,BNA案判決書的前後文也存在嚴重的邏輯問題。在前面,法官通過大段的論述,將三階段法與使合同有效的解釋方法區分開來,認爲前者是探尋當事人的爭議,後者是爲了“赤裸裸地使仲裁協議有效”。但在適用三階段法判斷本案的協議時,並未看出其在探尋當事人真實意思方面作出任何努力:從主觀解釋的角度來看,法官完全拒絕當事人合同談判的其他證據材料以及合同的初稿,從客觀解釋角度來看,對“在上海仲裁”一詞的解釋明顯偏離正常商業邏輯。相反,其極力試圖通過使用新加坡法“挽救”本案仲裁協議。從論證過程和結果來看,法官適用的在前文已被否定的方法來判斷案件,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最後,BNA案判決有導致裁決陷入不確定的危險。從本案的情況來看,雙方均爲中國內地主體,爭議內容似乎並無涉外因素,故裁決的執行也很可能會在中國法院進。中國法院在承認和外國仲裁裁決時,裁判的標准往往是國際公約、適用的仲裁規則乃至于中國法律,對于仲裁地國類似案件的判例並不會作過多的考慮,甚至可能因此作出和外國法院截然相反的判斷結果,在較早的如浙大網新案、較新的來寶案中,中國法院對于某些問題的判斷(如仲裁庭組成問題),與新加坡法院恰好相反,而中國法院在這些案件的執行過程中,也沒有對新加坡法院先作出的裁判意見作出過多的考量。因此,即使本案仲裁程序能夠繼續進行並順利作出裁決,本案裁決也很可能無法在中國境內執行,故當事人也只能獲得“皮洛士式的勝利”。
表面上來看,本案涉及仲裁地的判斷問題。但實際上,什麽是仲裁地反倒不是本案的關鍵問題,因爲法官自己似乎也無法堅持自己關于如何判斷仲裁地的觀點。在最後一段,他假設中國法律在合同簽訂後仲裁開始前進行了修訂,使得當事人的仲裁協議有效,那麽就不會有管轄權異議,仲裁程序也可以在以中國爲仲裁地、中國法爲仲裁協議准據法的基礎上繼續進行(判決第123節)。由此可見,新加坡法官作出這樣令人難以理解的法律選擇的原因,並非真的因爲當事人對仲裁地的約定存在問題,而是爲了使仲裁協議有效。這一做法雖然是基于“仲裁友好”,但由此曲解合同,並爲本案隨後的裁決以及今後的案例帶來不確定性,則很難說是仲裁界樂意見到的。
余論
對于案件本身的評價至此結束,但由本案延伸出來的一系列問題卻值得進一步思考,特別是新加坡法官所在最後一段所強調中國法下仲裁協議效力問題,給我們帶來了不小的啓示。
首先,在合同訂立方面,除了合同本身的約定以外,還應重視法律適用問題。長久以來,爭議解決條款被視爲“午夜條款”,並不爲當事人所重視,即使近年來開始被一些律師或者法務人員所重視,也往往著眼于其實際內容,對法律適用的重視也有所不足。而以BNA案爲代表的一系列案件說明,在一個法域中理所當然的有效協議,在另一個法域卻很可能無效。因此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的重要性並不亞于仲裁協議內容本身。更重要的是,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具有特殊性,不同國家適用的沖突規則並不完全一致。例如,在當事人沒有爲仲裁協議明確選定准據法的時候,中國法規定應以仲裁地或者仲裁機構所在地法爲准據法,不能適用主合同准據法;而在英國、新加坡等國,則默認適用主合同准據法,除非該法不利于仲裁協議有效。兩者在實踐中可能存在巨大差別,僅以“在福建廈門仲裁,適用英國法”的臨時仲裁條款爲例,在我國經三地法院四次審理後最終被認定爲無效(陳延忠:“在廈門仲裁,適用英國法”條款的曲折命運及其反思 ——申請人瑞福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與被申請人山東振宏能源有限公司案始末,載微信公衆號“采安律師事務所”2017年1月23日),但如果采取英國Sulamérica案、新加坡BCY案確立的三階段判斷法,則本案仲裁協議很可能因爲適用英國法而有效。由此可見,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給予法律適用更多的重視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次,我國法律和司法實踐中對仲裁協議效力認定的標准。比起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新加坡這樣比較受歡迎的仲裁地,我國現行立法對于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要求是比較嚴苛的,如必須約定仲裁機構、仲裁機構不能由兩個或以上等。而在司法實踐中,又爲仲裁協議的效力額外增加了一些要求和限制,例如本案所涉及的無涉外因素不能提交境外仲裁就是其中之一。這些要求和限制盡管出于各種目的,但都給仲裁協議的效力帶來了不確定性,加重了當事人的負擔,同時也與發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目標不符。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在仲裁協議方面作出了一些“松綁”的動作,在無涉外因素境外仲裁方面,2016年的《關于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允許法院有條件地在執行程序中認可自貿區注冊企業間的此類仲裁協議。在法律適用方面,2017年的《關于審理仲裁司法審查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引入了使仲裁協議有效的原則,規定法院在仲裁地法和仲裁機構所在地法之間選擇有利于協議效力的准據法。當然,要真正實現“仲裁友好”的目的,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本文認爲,仲裁裁決的可執行性雖然是國家法律賦予的,但根據法律(無論是民事訴訟法還是仲裁法),國家撤銷或者拒絕執行仲裁裁決都必須基于法律明確規定、窮盡列舉的理由,在現行法律尚未修改的情況下,法院至少不應對仲裁協議施加法律明文規定外的其他限制條件。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仲裁協議的獨立性確定仲裁協議准據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仲裁協議獨立性是目前各國普遍接受的原則,其意義在于保證仲裁協議不因主合同的效力存在問題而受到影響,從而保障仲裁庭的管轄權及仲裁程序的穩定。但在法律適用方面,我國和英國、新加坡等國對于仲裁協議獨立性的理解存在比較大的差異。BNA案再一次重申了新加坡法院的立場,即獨立性原則意味著仲裁協議的准據法與主合同准據法可以不一樣,但並非必然割裂,而在主合同准法可能導致仲裁協議無效的情況下,獨立性原則可以作爲保障仲裁協議效力的一道“防火牆”。而我國法院對此的理解則相對“形式主義”一些: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主合同准據法不能適用于仲裁協議,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58條明確指出:“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適用于解決合同爭議的准據法,不能用來確定涉外仲裁條款的效力”,其後的一系列立法、司法解釋及案例均基于這一論斷,完全拒絕將主合同准據法適用于仲裁協議,即使該准據法可能比仲裁地法更有利于仲裁協議有效。對仲裁協議獨立性理解的不同,可能導致中國與新加坡等國在法律適用結果上存在重大差別。
【萬邦仲裁】主編:何以堪
微信號:fishinarbitration
全球最新的法律仲裁資訊都在“萬邦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