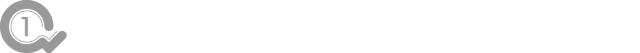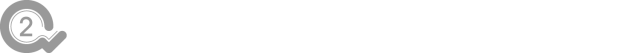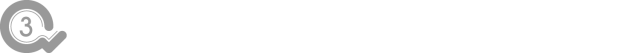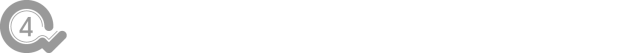·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3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從投資密集型增長轉變爲科技創新型增長——這是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討論中,海內外的一個共識。中國政府爲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制訂《中國制造2025》計劃。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中,美國一直要求中國停止對該計劃所涉及的先進技術領域提供補貼,美國的貿易懲罰措施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針對該計劃的。例如,在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發布的征稅産品建議清單中,在1300個稅號産品中,中國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航天航空、機器人、醫藥、機械等行業産品榜上有名,而中國形成貿易順差的普通工業品卻不在征稅名單中。可見美國的目標不完全是解決貿易逆差問題,而是針對《中國制造2025》所規劃的高端制造的發展。
本文將探討兩個問題:
首先,從美國的曆史看打壓中國高端制造是否明智;
其次,中國自身如何發展科技創新産業才能更加有效。
曆史上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美國向中國提出加強知識産權保護,以及平等的産品和資本市場准入,我認爲這些都是合理的訴求,但美國打壓中國高端制造業是極其不明智的。科學和技術是沒有國界的,在産權保護、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一個國家在科技方面的進步不光讓科技提供方受益,也讓科技需求方受益。美國在互聯網、生命科學、新材料等領域的創新,受益方不止是美國,中國以至世界都是受益方。在市場經濟和法治前提下,如果中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航天航空、機器人、醫藥、機械等行業産生創新,取得突破,這將造福全人類。
美國不應阻擋中國的科技發展,而應以“舉國之力”支持自身的科技發展。《中國制造2025》應該成爲美國21世紀的“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中美在科技領域展開符合法治和市場經濟准則的競爭,將會加快科技發展和科技産業化的步伐。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應該歡迎這場競爭。
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Sputnik,俄語含義爲“伴侶”)。當時正值冷戰對峙時期,斯普特尼克一號的成功發射在美國引起極大震動,並引發了一系列事件,史稱“斯普特尼克危機”。
1958年7月29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正式批准成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並推動了載人航天計劃“水星計劃”。美國中學數學教育更是進行了名爲“新數學”的大改革,以加強美國學生的科學和數學能力。在很多美國人看來,蘇聯之所以發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蘇聯擁有一批優秀的數學家。
1959年,美國國會撥付了1.34億美元給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億美元。到1968年,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預算已經快速上升到近五億美元。
斯普特尼克一號的發生成功震撼了美國,促進他們加大科學領域的投入,與前蘇聯進行太空競賽,並加強自身科技實力。
現在,前蘇聯早已不在,而美國因爲“斯普尼特克危機”建立的NASA卻是世界最強大的科研機構。上世紀60年代美對航空科學領域的投入,更帶動了美國整體科學的發展,促進了美國微電子、集成電路、通訊行業的急速崛起和商業應用。可以肯定,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奠定了美國今天科技和商業的領先地位。
什麽在摧毀美國的科技實力?
今天美國的明智做法,應該是以《中國制造2025》和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爲契機,大力扶持、推動美國自己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産業創新,和中國展開正面的科技和先進制造業的競爭。但特朗普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非但沒有大力扶持本國創新,卻在削減國家對科技研究的投入,大力發展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標志煤炭産業,爲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再生能源創新設置重重壁壘。不僅如此,共和黨通過的稅法史無前例地還要對大學——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征稅。
根據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數據統計,美國聯邦政府對于非國防類研究發展(R&D)的經費投入在過去15年裏一直保持在每年70億美元左右的水平,沒有明顯增長。考慮到美國平均每年2%左右的通脹率,這一經費投入其實是每年在縮水的。而從占GDP的比重來看,美國聯邦政府對于研究投入的縮水程度更是顯露無疑。聯邦政府對于研究發展經費的投入從1976年占GDP的1.2%一路跌到2018年的0.7%。
我們可以做一個橫向對比,歐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諸如芬蘭、瑞典和丹麥,每年政府對于研究發展的投入都維持在GDP的1%以上。美國的研發經費投入每年都在縮水,從長遠來看,顯然不足以幫助美國持續保持創新強國地位。
不僅是研究發展領域,美國聯邦政府對于教育經費的投入也越來越吝啬。2018年2月,特朗普發表了其對2019年美國預算的陳述,計劃削減3.6億的美國教育預算,相當于大約減少5.3%。
在2017年12月通過的美國稅改中,特朗普更是史無前例地決定,對美國私立大學所接受的捐款增稅。法案中寫明,如果接受捐款的私立大學擁有500名學生以上,且學生人均從捐款獲益超過50萬美元,那麽美國聯邦政府就將對捐款征收1.4%的稅。受此影響的大學包括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這樣的頂尖研究性學府。
在此之前,因爲大學是非盈利組織,美國從未對大學征過稅。對于私立大學,私人捐贈是學校獲得經費的最重要途徑,對其征稅,相當于削減了美國頂尖私立大學的財政預算,會影響到大學的日常教學和研究項目。
美國政府非但不增加研究經費的實際投入,反而對頂尖研究型的私立大學征稅,這將挫傷科研領域的積極性和實力。科技和教育具有極大的溢出效益,它們的發展是需要政府和社會大量支持的。
2005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的研究報告《站在風暴之上》指出,美國的繁榮,得益于美國聯邦政府對高校、企業和國家實驗室科學研究的大力支持。全球競爭的核心是創新能力。美國在二戰後形成的國際霸主地位,離不開其對于科學研究的支持和其強大的創新能力。
美國科技的領先歸功于它的軟實力,它可以從全世界吸引優秀的人才,包括在“二戰”後吸納了德國的優秀科學家。然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卻要限制研究人才進入美國。一邊限制移民,一邊削減對于研究和教育的投入。真正摧毀美國科技實力的不是《中國制造2025》,而是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政策。
美國在知識産權保護和市場准入上對中國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中國真正想成爲一個創新國家首先要解決的正是知識産權的保護和市場競爭的問題。
發明和創造是沒有國籍的,保護了美國的發明者也就是保護了中國自己的發明者。誰都可以去發明,但壟斷是不會促進發明産生的。
美國正確的國策應該是和中國政府提出和討論遊戲規則的問題,而不應該去壓制中國的創新。美國同時應該以《中國制造2025》爲契機,加大國內科研投入和扶持力度,鞏固美國的創新能力,和中國正面競爭。但是共和黨領導的美國沒有做出這樣的選擇,沒有將挑戰變成機會,因此也就沒有使美國擁有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
爲什麽學習新加坡?
在談完美國之後,我們再來介紹兩個國家。在我看來,這兩個國家的例子將幫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創新的下一步方向。
這兩個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人口都不多,一個國家的人口只有564萬(包括外籍居民),另一個也只有899萬。兩個國家的主體民族人口都占全國人口的大約75%;
其次,兩個國家經濟都十分發達,其中一個人均GDP達到64030美元,另一個也達到41400美元;
還有,這兩個國家的國家安全都曾長期受到外部威脅,都實行強制性征兵。其中一個國家曾經和它的鄰居同屬一個國家,但後來卻被投票驅逐,當時的中央政府認爲該地的主體民族會威脅其旁鄰的政治影響力更大的主體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個國家則處在被敵對國家包圍的地理環境之中。
各位讀者也許已經猜出了這兩個國家的名字。一個是新加坡,另一個是以色列。
爲什麽要在一篇關于中國創新模式的文章中提到這兩個國家?事實上,雖然中國堅持獨特的發展模式,但一直推崇向新加坡學習。
新加坡是個小國,但這從未成爲中國官員將其視爲榜樣的顧慮。1978年訪問新加坡期間,鄧小平先生就呼籲中國學習新加坡的經驗,他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又一次提到學習新加坡的“良好的社會紀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敗的方式,往往被中國政府視爲控制自身腐敗問題的參照,與此同時,中國官員經常將新加坡政府運營的投資公司淡馬錫(Temasek)作爲管理國有資産的典範。
據新加坡總統陳慶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兩國會晤上的介紹,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15年,有超過5萬名中國官員赴新加坡學習城市管理、社會治理和公共管理等。
最著名的中國官員培訓項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提供的培訓課程。
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經濟學兩個中文碩士學位課程,因其招收的中國市長和潛在市長接班人衆多,而被稱爲“市長班”。
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劉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底,大約1400名中國官員畢業于南洋理工大學的“市長班”。他說,該校還提供短期項目,培訓了1.5萬多名來自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官員,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新加坡是一個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來實現經濟增長,同時保證廉潔政府的典範。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認爲政治競爭和公開披露是控制腐敗和提供良好治理的關鍵。它采取嚴厲的懲罰措施,並輔以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機制,以吸引頂尖人才成爲公務員,同時控制腐敗。
我不否認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認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唯一的學習模式?這是值得商榷的。
以色列的比較
因此,我希望將以色列這個國家納入比較。
以色列是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以色列模式是對一個很普遍看法的證僞,即應付險惡的生存環境必須集中權力。
以色列通過自身的發展證明,民主能夠在一些最具挑戰性的地緣政治條件和最敵對的國際環境中生存,甚至繁榮。
以色列的政治經常是混亂的、快速變化的和不可預測的。它沒有新加坡的淡馬錫,但也不需要這樣的組織。它的民企發展的足夠強大,完全獨立。它的大學體系也享有獨立和學術自由。
我們在向與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學習,因此,我們顯然無法從邏輯上用以色列是個小國作爲借口而拒絕學習。和政府官員對新加坡的青睐不同,對中國的創新創業界來說,以色列才是一個模範國家。盡管有超過5萬的中國官員前往新加坡(2015年數據),但中國的技術人員和投資人則紛紛前往以色列。
中國在以色列的投資額正在迅速增長。根據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過去兩年,中國投資者在以色列的投資活動穩步增加,從平均每個季度15筆投資增加到大約20筆。2018年第三季度,中國投資者參與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與過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中國企業傾向于投資軟件和生命科學等“主流”行業,傾向于投資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強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國投資者參與了以色列規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截至11月已投資3.25億美元。而2017年爲3.08億美元,2016年爲2.74億美元。
雖然新加坡仍然吸引著中國的國有大型企業和政府機構,但中國的科技公司,如阿裏巴巴、百度、複星、聯想和小米,已經或即將在以色列開設研發中心。過去5年裏(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躍的中國投資者是維港投資(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筆交易;緊隨其後的是CE Ventures,有19筆交易;然後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筆交易;阿裏巴巴則有12筆交易。
2018年中國成爲以色列第二大投資來源,僅次于美國。在期待更多中國投資的同時,不少以色列企業尤其是科創企業,也盯上了中國的市場。
結語
新加坡與以色列的對比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控制、人爲秩序與自下而上的活力、自發秩序和群體智慧之間的對比。
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適合中國發展以高速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爲主的增長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國創新下一步的發展方向,中國企業家的行爲表明中國願意接受以色列的技術和發明。
將增長模式由投資驅動轉變爲由技術驅動,不是打開一個“魔法盒子”的技術開關,然後搖身一變就成了。中國要實現技術驅動型增長,必須在以下領域做出更多的切實努力:
-
實行法治;
-
加強知識産權保護;
-
履行合同;
-
尊重學術自由和獨立;
-
最重要的是,減少和限制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中的直接的幹預。
-
作者爲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他對中美的政經觀察等內容經常刊登在微信公衆號“亞生看G2”上。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秦朔朋友圈微信公衆號:qspyq2015
商務合作:[email protected]
投稿、內容合作、招聘簡曆:[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