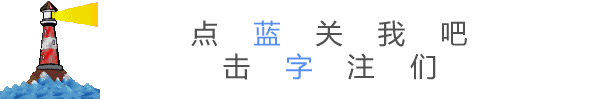【內容提要】中國參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建設,形成了“商業港口鏈”,與美國在海上絲路沿線構築的“軍事基地鏈”形成反差。前者服務于中國與對象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以投資、貿易、基建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等商業利益拓展爲目標;後者服務于美國的安全戰略,以鞏固聯盟體系、打擊恐怖主義、拓展勢力範圍、扶持代理人爲主要目標。中國從自身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蛇口模式”出發,爲海上絲路沿線新興國家的和平與穩定貢獻中國方案——以發展促安全,在實踐中探索中國特色的港口外交。中國的港口外交以企業爲主體、以市場爲導向,以政府各部委、中央與地方統籌協調爲保障,促進了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陸海聯動”,有助于各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建立相互依存關系,超越“零和博弈”與“中心—邊緣”的非對稱依賴關系。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推動了對象國的“工業化”進程,彰顯中國特色的民生治理理念,與西方追求的“海洋軍事化”和民主治理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在未來仍將面臨較高經濟、法律、政治和安全風險,須警惕港口建設的“政治化”趨向。
【關鍵詞】港口外交;“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港口政治;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孫德剛,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上海 郵編:200083)
JELClassification:F15; F41; F55
一、導 言
中國是陸海兩棲型大國,兼具海上與陸上對外交往的雙重優勢。早在唐朝時期,福建泉州就是東方第一大港,商賈雲集,成爲溝通東西方交通和海上貿易的橋梁和紐帶。2010年以來,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名列前茅的貿易強國,逐步從淨資本輸入國變成了淨資本輸出國,優勢産能不斷增加。港口、公路、橋梁、核電站、高鐵、北鬥衛星等是中國海外利益拓展的重要載體,也是中國“大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工具箱”(潘玥,2017;胡鍵,2015)。
參與海外港口建設是新時代“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內容。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海洋強國研究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組成部分。中國從海洋大國崛起爲海洋強國,從港口大國邁向港口強國,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截至2016年底,在全球50大集裝箱港口中,中國投資了其中的2/3。[1]中企參與經營的港口項目遍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澳大利亞、緬甸、斯裏蘭卡、巴基斯坦、阿聯酋、肯尼亞、吉布提、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希臘、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多哥、安哥拉、西班牙、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等二十多個國家。如作爲中國港口企業的先驅,招商局港口(原招商局國際)海外總投資超過20億美元,其投資的49個港口分布在19個國家和地區;中遠海運港口(原中遠太平洋)在全球投資近30個港口,其中“一帶一路”沿線碼頭共11個。[2]
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的港口建設,體現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建設者、工業化的推動者和區域一體化的參與者。中國在海上絲路沿線國家港口建設形成的商業存在,與西方大國的軍事基地、軍事聯盟和軍事幹預形成的三位一體的軍事存在形成鮮明對比。作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橋頭堡,港口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引擎(管清友,2015)。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對于國際能源運輸線、工業貿易品運輸線和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實際上是歐、亞、非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它是以發展中國家爲主體的“再全球化”,港口則是歐、亞、非國家交通基礎設施相互依存的關鍵點。
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項目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國參與地區治理和擴大中國在海外經濟存在的重要平台,卻常常被西方妖魔化爲所謂謀求地緣政治利益的“珍珠鏈”;美國國防部甚至列出了所謂“珍珠鏈”中的五顆“珍珠”: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斯裏蘭卡的漢班托特港、緬甸的秘密海軍基地、泰國克拉地峽運河等,這些大多與海上絲路沿線中國參與的港口建設息息相關(曹文振、畢龍翔,2016)。近年來日本、印度等國媒體也對中國建設海上絲路沿線港口的戰略意圖存在疑慮,指責中國的港口投資缺乏透明度,且中國參與的港口建設加重了當地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導致對象國不得不在經濟上依靠中國,甚至形成新的“中心—邊緣”不對稱依附關系。他們斷言,近年來中國參與斯裏蘭卡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導致該國對華負債超過80億美元,不得不將漢班托特港99年經營權轉讓給中企;中國在海外港口建設中正推行所謂“債務帝國主義”(Creditor Imperialism)。[4]
在海外港口建設過程中,如何打消西方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建立所謂“珍珠鏈”、奉行“債權帝國主義”、推行中國版“門羅主義”的憂慮?如何既堅持中國傳統的防禦性外交原則,又能積極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促進互利發展?這無疑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特色的港口外交:內涵與範式
中國特色的港口外交根植于中資企業參與海外港口建設的豐富實踐,與中國外交決策體制、中國國有港口企業占主體地位、中國優勢産能對外轉移存在重要關聯。隨著中資企業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不斷走向深入,中國港口外交的輪廓也日益清晰。通過鐵路、公路、橋梁和港口等基礎設施網狀化發展,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正形成陸海聯動、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密切聯系、安全議題與發展議題相互促進的港口外交。
中國的港口外交系指“中國與對象國著眼于發展戰略對接,在港口建設中充分發揮各方優勢,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各部門與企業相互配合,使中資企業在參與海外港口建設過程中服務于外交戰略目標,從而實現中國政治需要、企業利益需要和對象國發展需要的理念、機制和政策總和”。中國港口外交的範式具有四重性:一是政府與企業的良性互動;二是政府各部委之間的統籌協調;三是中央與地方的相互支撐;四是中國與對象國的互利合作。
第一重:政府與企業關系。中國參會海外港口建設的企業大多屬于大型國有企業,與政府的對外戰略目標具有高度一致性。一方面,港口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配合中國的總體外交規劃,成爲落實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港口合作的重要主體,豐富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工具箱”;另一方面,外交部等各部委在政府間合作過程中積極營造良好的政治和外交環境,成爲中國港口企業拓展海外利益、參與海外港口建設的“代言人”,爲中國港口企業走出國門、輸出資本和轉移優勢産能提供政策、融資和外交保障。在政企互動模式下,港口外交互爲政府與企業的手段和目的。2015年11月,李克強總理訪問馬來西亞,與納吉布總理共同見證了中馬兩國港口聯盟合作備忘錄的簽訂,就是政企互動的重要表現。[5]
在中國港口外交實踐過程中,政府與企業互動日益頻繁,中國港口管理體制也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後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全國港口由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其弊端是港口缺乏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積極性未能充分調動起來。21世紀初,這種高度集中的港口管理模式開始發生轉變,中央將港口管理下放給所在城市,形成“政府引導、地方主導、企業參與”的三重領導管理體制。這種新型管理模式對推動港口與産業的良性互動起到了積極作用(趙楠、真虹、謝文卿,2016)。2004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簡稱《港口法》)付諸實施,2015年修改,爲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港口建設、爲港口企業“走出去”和中國開展港口外交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二重:政府各部委之間關系。在“一帶一路”總體框架下,中央各部委如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交通運輸部等圍繞中國企業參與海外港口建設,既有分工,又相互協調與統籌。21世紀初以來,中國港口外交的頂層設計不斷成熟。2011年國務院審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對港口尤其是國內港口發展進行了總體規劃,提出要“提升沿海港口群的現代化水平”,“深化港口岸線資源整合和優化港口布局”。[6]2012年11月,胡錦濤主席指出:“要提高維護海洋安全的戰略能力,捍衛國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保護國家日益發展的海洋産業、海上運輸和能源資源戰略通道安全”(梁芳,2011);2013年7月,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既是陸地大國,也是海洋大國,擁有廣泛的海洋戰略利益……我們要著眼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陸海統籌,堅持走依海富國、以海強國、人海和諧、合作共贏的發展道路,通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方式,紮實推進海洋強國建設。”[7]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雖未專門論述中國參與海外港口建設,但提出,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造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大通道建設,共同建設國際經濟合作走廊。[8]中國出台的一系列文件成爲各部委圍繞港口合作的指導性文件。發改委國際合作司[9]、外交部各地區司(包括海上絲路沿線的亞洲司、西亞北非司、非洲司、歐洲司等)、商務部各地區司(如亞洲司、西亞非洲司、歐洲司)、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成爲落實黨中央戰略部署的主體機構。
外交部、交通運輸部、商務部等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互配合。2014 年10 月,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任爲民在深圳舉辦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合作論壇及第四屆深圳國際港口鏈戰略論壇”上表示,沿線國家和地區間港口投資建設運營合作,是未來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方向。港口外交除了向巴基斯坦、斯裏蘭卡等國家提援助建設港口碼頭外,還包括承建海外港口項目、獲取港口經營權、建設港口等參與方式。[10]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也積極協調與統籌,于2015年3月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強調港口在海上絲路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提出:“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爲支撐……海上以重點港口爲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推動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暢通陸水聯運通道,推進港口合作建設,增加海上航線和班次,加強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11]
第三重:中央與地方關系。中國是陸海兩棲型大國,東部沿海地區與西北內陸省份發展不平衡。爲促進西北、東北、西南省份對外開放,中央政府在對外交往中爲上述內陸省份對外開放積極創造條件。參與海外港口建設不僅有利于對象國,而且通過互聯互通促進中國內陸省份的陸海聯動發展,使國外港口建設成爲跨國界、跨地區合作的典範。內陸省份通過與沿海地區、或跨境沿海地區建立互聯互通的經濟一體化,響應國家發展戰略,落實國家的頂層設計藍圖和規劃。
在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拉動內陸地區經濟發展問題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一致的。首先,在內陸地區,中國參與瓜達爾港建設,通過“中巴經濟走廊”將西亞、南亞等海上諸國與中國新疆、阿富汗、中亞等內陸地區連爲一體;中國建設緬甸皎漂港,將中國雲南內陸、緬甸內陸地區與印度洋海上運輸線連爲一體,縮短海上航程,促進互聯互通;中國租用朝鮮羅津港,旨在實現東北企業“借港出海”,爲東三省、內蒙古、乃至蒙古國等內陸地區與海洋經濟相聯系提供了通道。其次,在沿海地區,港口成爲新時期中國外交的重要載體,建立“友好港”是中國港口城市參與海上絲路建設的重要方式。2015年,中國政府公布了新時期中國重點建設的15個港口,由北向南分別是:大連、天津、煙台、青島、上海、甯波、福州、泉州、廈門、汕頭、廣州、深圳、湛江、海口和三亞。[12]上海港、青島港、深圳港、連雲港等多個港口公司開始通過“友好港口”、合作運營等形式積極在“一帶一路”沿線進行相關合作,召開港口論壇,建立港口合作聯盟,成爲中國地方參與海外港口建設與運營、配合中央開展“港口外交”的重要依靠力量。例如,青島與海外16家港口建立“友好港”,成爲港口外交的地方支撐力量。
第四重:中國與對象國關系。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經濟模式和中長期發展戰略等領域差異甚大,但是加強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拉動就業、促進沿海與內陸地區聯動發展、改善民生是中國和對象國的共同訴求。中國開展港口外交、中企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實際上是在推廣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蛇口模式”,試圖在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過程中加以推廣:即“前港—中區—後城”相互配合,向縱深發展;在硬環境建設方面,建設一流的港口設施,打通港口與腹地之間的集疏運通道,開發産業園區、物流園區、自由貿易區等,建設産業發展所需的商業配套設施和生活配套設施;在軟環境建設方面,提供通關、結算、支付、物流、培訓等服務。[13]
中國是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的建設者,港口建設彰顯民生治理的優勢。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當地就業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有助于緩和社會矛盾,化解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爆發大規模社會動蕩乃至發生政權更叠的風險。
三、中國開展港口外交的優勢與影響
中國的港口建設經曆了“請進來”和“走出去”兩個階段。在前一個階段(1949-1999),中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建設國內港口,是港口外交的准備階段;第二個階段(2000年至今)爲中國優勢港口企業走出去、建設國外港口,是港口外交的實踐階段。
21世紀初以來,中國港口事業的發展進入第二階段,中國從港口大國邁向港口強國。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尤其是隨著中國國內港口技術的升級和建設能力的提高,中資港口企業憑借優勢産能和豐厚資本,開始走出國門,參與發展中國家乃至發達國家的港口建設、探索港口外交的新範式。
中國開展港口外交優勢明顯。首先,中國在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能力方面占據優勢。中國是世界上頭號造船大國;自2013年開始,中國躍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中國港口貨物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連續十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貨物吞吐量前20大港口排名中,中國大陸港口占13席;在全球集裝箱吞吐量前20大港口排名中,中國大陸港口占8席。[14]2014年,中國外貿出口達2.35萬億美元,其中80%經過海上運輸,港口在中國海上貿易中占據重要位置(Eran, 2016)。截至2016年底,中國港口萬噸級以上的泊位2317個,設備最先進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動化碼頭2017年底投入使用;青島港40萬噸礦石碼頭、甯波舟山港45萬噸原油碼頭、廣州港南沙集裝箱三期、重慶果園港等重點項目陸續投入使用。[15]中國億噸大港達34個,在全球港口貨物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的港中,中國港口占7席。
中國在港口建設方面的優勢産能,已經轉化爲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的重要生産力。如斯裏蘭卡科倫坡港花了幾個世紀才達到其今天的吞吐量,而中國建設科倫坡港後,在短短的30個月內就使其港口吞吐量翻了一番,並有望在未來建成世界前三十大港口,體現出中國作爲港口建設大國的技術優勢和建設能力;中遠集團參與建設的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促進了該國與中東歐國家的互聯互通,提升了該港口的航運中心建設,拉動了這個深陷債務危機國家的投資和就業,有助于該國盡快擺脫經濟危機。[16]
其次,海上絲路沿線擁有衆多天然不凍港、深水港和陸地戰略縱深,港口開發潛力巨大。2002年以來,中國參與的2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2013年占3個,2014年占5個。[17]據《金融時報》的統計,2010年,中國投資了全球50大港口中的1/5;到了2015年,中國則投資了全球50大港口中的2/3[18],表明中國港口建設與運營能力已越來越被世界其他國家所認可。“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 億,經濟總量約21 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19]這些大多屬于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天然良港,港口開發資源豐富。例如,近年來非洲大陸基礎設施建設對GDP的貢獻率超過了50%,但資金缺口大,每年至少需要930億美元。吸引外資參與絲路沿線港口基礎設施建設,對于這些國家的經濟騰飛和社會穩定意義重大(Foster and Garmendia,2010)。
新時期中國以商業港口建設爲依托,既擴大經濟存在,又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奠定基礎,中資企業參與海外港口建設與中國“建設互聯互通世界”的外交目標高度契合。
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的港口建設實踐,豐富了中國港口外交理論,使政府與企業、外交部與其他部委、中央與地方、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形成了重要“共生關系”,它有別于“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對抗式、零和性冷戰思維,也不同于“贏者通吃、互害”的實踐模式(蘇長和,2016)。中國參與建設的巴哈馬北阿巴科島新建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澳大利亞達爾文港、肯尼亞蒙巴薩港、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和孟加拉國吉大港等均位于國際航運中轉站,均有助于對象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民生改善。
在東南亞—南太平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這一海上絲路沿線,存在兩條鏈,一是美國部署的“軍事基地鏈”,以安全利益爲訴求;二是中國參與建設和運營的商業港口鏈,以經濟利益爲訴求,尋求包容性發展。中遠海運港口、中國港灣、招商局港口、中國交建、中國海外港口、中國路橋、山東岚橋、上港集團等十幾家中資企業在海外參與了20多個國家的港口建設與運營,成爲中國建設藍色海洋經濟帶、促進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重要支點。總部位于倫敦的格裏森高端投資銀行(Grisons PeakInvestment Bank)研究顯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中資企業宣布了9個海外港口收購或投資計劃,相關項目總價值高達201億美元。與一年前同期的99.7億美元中國海外港口項目總價值相比,翻了一番。[20]
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港口外交中的“民生治理”與“互聯互通”理念已逐步爲海上絲路沿線國家所理解和接受。中遠集團建設和管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與橫跨匈牙利、塞爾維亞、馬其頓和希臘的“中歐陸海快線”連爲一體,促進了巴爾幹與中東歐陸海聯動發展;中國建設的肯尼亞蒙巴薩港系東非第一大港,其不僅通過鐵路與內羅畢相連,帶動肯尼亞內陸地區的發展,而且服務于烏幹達、盧旺達、布隆迪、南蘇丹、剛果(金)和剛果(布),成爲東非及其他非洲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窗口(甄峰等,2014);中國建設的吉布提港,與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鐵路線連爲一體,爲內陸國埃塞提供了出海口;中國在坦桑尼亞和尼日利亞的港口建設,也都與東道國的鐵路線相連,實現陸海聯動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王德華,2015)。中國港口外交的民生優先理念比美國基地外交的民主優先理念更有吸引力。
從中國港口外交的實踐可以看出,中美對導致發展中國家沖突的根源理解不同:美方認爲地區沖突的根源是缺乏民主,即所謂“民主赤字”(Elbadawi and Makdisi,2010),因而解決地區沖突的“本”是制定民主、法治政體,改善沖突地區的人權;中國則認爲地區沖突的根源是經濟和社會矛盾,因而解決地區沖突的“本”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政府認爲,美方解決地區治理的理念體現出西醫式的“治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國的地區沖突治理理念體現中醫式的“治本”,以經濟社會發展促安全(孫德剛,2015)。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屬于經濟和投資範疇,更有助于當地國家的政治穩定與安全治理。
新時期中國的港口外交屬于經濟外交的範疇,在目標上選擇經濟和外交的雙重融合模式,即外交工作服務國際經濟合作,利用國際經濟合作來實現外交目標;在路徑上促進國際和國內議程的相互協調與統籌;在實踐中推動市場—國家的協力共進(複旦國務智庫,2016)。隨著中國港口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和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不斷走向深入,中國特色的港口外交將産生深遠影響。
首先,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有助于提高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水平。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參與海外港口建設成爲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在未來五年裏,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合作夥伴與戰略支點,對實現“十三五”規劃宏偉目標——“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加快産能轉移與國際産能合作、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起到重要作用。海上絲路沿線的港口建設從長遠來看爲實現中國向西開放,加強與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産能合作,促進發展戰略對接,將發揮積極作用。
其次,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有助于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的“再全球化”。“一帶一路”是中國發起的倡議,它打破了數百年來西方主導的“中心—外圍結構”和不均衡的全球化,成爲發展中國家推動的“再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到新階段的産物。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從港口大國向港口強國邁進。“一帶一路”是中國首次提出的重大經濟發展倡議,是持續推動中國崛起的發展方略,也將成爲21世紀發展中國家“再全球化”的推動力量(趙洋,2016;馮並,2015)。
再次,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有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穩定。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絕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率高,就業壓力大,社會矛盾尖銳,政局不穩,但是發展潛力巨大。大部分絲路沿線國家擁有1-2個主要港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阿聯酋等貿易發展相對好的地區除現代化程度高的主要港口外,在區域內還輔以一定數量的一般港口等待開發。從中國南海到印度洋,從紅海到地中海,大部分港口物流績效低,潛力尚未完全挖掘,如東南亞的緬甸和柬埔寨;南亞的孟加拉國、巴基斯坦、斯裏蘭卡;西亞的也門、伊朗、敘利亞;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而非洲港口的效率更是普遍偏低(謝文卿、趙楠,2016)。中國參與發展中國家的港口建設,體現出“中醫式治理”理念,即發展是解決發展中國家主要社會矛盾的總鑰匙;民生是國家治理的關鍵;港口振興是拉動內陸地區經濟騰飛的引擎。2016年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羅阿盟總部演說,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的“中醫式治理”:“破解難題,關鍵要加快發展。中東動蕩,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發展事關人民生活和尊嚴。”[21]
最後,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有助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海上能源與通道安全。東南亞—南太平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進口的80%石油、50%的天然氣和42.6%的進出口商品都要經過這條航線,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方向(劉宗義,2014)。如果說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的“血脈”,港口自然成爲注入國際新鮮血液的重要“血管”(管清友,2015)。近年來海上絲路沿線亞丁灣海盜問題,“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及其在索馬裏、也門、西奈半島、東南亞分支機構引發的恐怖主義問題,巴基斯坦和緬甸民族分離主義問題,斯裏蘭卡、馬爾代夫等國內局勢動蕩問題,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國內沖突問題等,嚴重影響海上能源與通道安全。中國參與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對于維護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土耳其海峽、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海峽的石油和貿易通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助于中國在海洋領域提供安全公共産品。中國以港口爲重點,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港口—鐵路、港口—工業園區等建設模式,必將帶動中國標准和中國設備的出口,發揮中國的産業優勢。同時,中國建設的港口將爲中國船只提供補給和修理服務,助力中國維護海上運輸安全和提高對關鍵性航道的保護能力,彌補美、歐、俄等域外力量在安全公共産品領域的供給不足(張潔,2016)。
四、中國特色港口外交的特征歸納
海外港口建設既涉及經濟問題,又涉及政治問題;既涉及國家治理議題,又涉及全球治理議題;既涉及國內政治問題,又涉及國際政治問題。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實踐豐富,總體上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府與企業良性互動。從中國港口企業的海外投資實踐可以看出,中遠海運港口、招商局港口、中國港灣、中國路橋等企業追求商業利益,政府爲企業保駕護航;政府追求政治利益,加強頂層設計,企業作爲重要踐行者。近年來中國領導人訪問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包括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和部長等),與海外港口項目的簽訂和落實的時間節點高度一致;中國領導人將簽訂港口開發協議作爲重要訪問成果,體現出港口外交中的政企關系。同時,在海外港口招標和實施的重要時間點,中國政府還常常邀請對象國總統、總理訪華、出席多邊會議等,爲中資港口企業拓展海外業務搭建平台。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港口外交與高鐵外交具有高度相似性。
除領導人互訪外,中國政府還通過出台優惠政策、融資等方式,積極鼓勵港口公司在海外拓展業務。2017年1月,國家開發銀行向中遠集團提供了1800億元人民幣的信貸,用于拓展國際航運業務。2010年以來,中遠集團、招商局港口、中國海外港口公司對外投資已超過40億美元,收購了世界50個最大集裝箱港口中的21個港口股份,並向國內港口注資400億美元。正如西方一家港口公司高管所言:中國人可以進行更遠期的規劃,也可以與亞非某些敏感國家簽署協議;而外國私營管理公司做投資計劃時最多考慮今後12個月,尤其是受制于股東的意見和公衆輿論,西方企業卻不可能去某些國家投資。[22]
中國大型國有港口企業參與海外港口建設與中國對外開放的目標一致。新時期中國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既可以做到以商業港口建設爲依托,擴大經濟存在,又可以爲新時期中國提升大國地位、增強全球治理能力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使中國作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能夠在東南亞—南太平洋—印度洋—紅海—地中海—大西洋地區發揮獨特影響力(孫德剛,2014)。中國在吉布提獲得後勤保障基地,與招商局港口參與吉布提港口建設、爲此“打前站”存在重要關系。中國建設瓜達爾港和“中巴經濟走廊”,爲阿富汗和中亞國家油氣與商品出口提供出海口,把瓜達爾港打造成中亞、中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互聯、互通、互用的“共享港口”,密切了中國、阿富汗和中亞國家的政治關系。
第二,中央各部委統籌協調。中國國家主席、總理、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等率團訪問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簽訂港口合作協議,往往都會請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交通運輸部的負責人一同前往,共同參與研討和規劃馬來西亞、文萊、希臘、斯裏蘭卡、緬甸、埃及、比利時等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的重點項目。當然,這些判斷主要基于媒體的公開報道,發改委國際合作司,外交部亞洲司、西亞北非司、非洲司、歐洲司,商務部亞洲司、西亞非洲司、歐洲司,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等諸機構內部如何進行統籌和協調,“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如何對內進行統籌和協調,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中央與地方相互支撐。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體現出中央和地方的密切合作關系。山東、廣西、河北、浙江和上海等沿海地區以山東岚橋、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河北港口集團、甯波舟山港集團和上港集團等爲依托,在中央“一帶一路”的總體布局下,積極拓展海外業務,促進了海上絲路基礎設施項目的落地生根。
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也著眼于內陸地區的開發和開放。通過海外港口開發,內陸地區可參與中央規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尤其是西南、華南、西北地區成爲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的重要受益者。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學界存在陸權優先與海權優先的爭論。大多學者采取二分法,將陸權與海權對立起來,要麽陸權優先,要麽海權優先。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旨在促進陸權與海權的融合。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是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促進中國與歐、亞、非陸海國家之間的貿易暢通、相互依存與陸海聯動。如直通日照港的新菏兖日鐵路向西與隴海鐵路相彙,從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經中亞、西亞直達荷蘭鹿特丹;中國第一條重載鐵路山西中南部鐵路也直達港區。連接港口的疏港高速與日蘭、沈海高速公路相通,4 條國道幹線通往全國各地(杜傳志,2016),形成公路—鐵路—港口運輸網。
港口是連接沿海與陸地、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平台。擴大港口腹地範圍,是港口爭取區域性樞紐港地位的重要舉措。港口航運業的發展帶動了港口城的興起,成爲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Hall, et al.,2016)。近年來,東盟國家以港口建設爲平台,促進“陸上東盟”與“海上東盟”之間的互聯互通(汪海,2007);中國提出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旨在通過港口網、鐵路網和公路網建設,把中國、東盟和南亞經濟體連爲一體,實現東南亞和南亞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中國建設緬甸皎漂港,帶動了中國西南省份的對外開放。中、緬、韓、印投資的緬甸西南海域的天然氣管線首站——皎漂分輸站,經過793公裏的管道輸往雲南省,也是企業利益與政府利益相得益彰的重要體現(王德華,2015);中國建設瓜達爾港帶動新疆的經濟發展,既落實了“中巴經濟走廊”宏偉藍圖,又增強了西北省份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國家的互聯互通。
第四,中國與對象國互利合作。中國和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圍繞港口建設的合作,體現出彼此戰略對接,特別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對象國的發展戰略相對接,如埃及塞西政府的“經濟振興計劃”,沙特的“2030願景”,土耳其的“2023目標”等,體現出中國和對象國在民生治理領域的合作。
隨著中國港口企業走出去,民生優先的“中醫式”治理理念已被越來越多國家所接受。2016年5月,王毅外長在多哈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講話指出:要讓鐵路和港口成爲中阿交往的標志。中方支持中資企業參與阿拉伯半島和北非鐵路網建設,支持中國有關省區與阿拉伯重要港口城市共建友港。中方願與阿拉伯國家共同推動産港融合,按照“港口+工業園區”模式,把地區條件優良的港口建成集經濟開發、貿易合作、工業生産等一體的綜合基地。[23]如吉布提人口僅90萬,但失業率高達48%,42%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近年來對吉港口和機場投資達到了120億美元,不僅改善了該國民生,而且帶動了就業和經濟增長,緩解了社會矛盾,爲非洲中小國家的發展樹立了榜樣,有望將該國的港口建成“東非的新加坡”(Jeffrey,2016)。
五、結論
中國傳統上屬于農耕文明,在治國理念上存在“重農輕商”、“重陸輕海”、“重塞防輕海防”的局限性。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加速從傳統的“內向型經濟形態”向“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形態”轉變(王曆榮,2009)。21世紀初,中國更加重視海上戰略通道與海洋強國建設。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不僅可以轉移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産能,而且可以倒逼中國港企的技術升級換代。
中國參與國外港口建設既積累了豐富經驗,也有若幹教訓值得認真總結。一方面,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和戰亂國家基礎設施重建,促進海上經濟的互聯互通,是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的動機;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緬甸實兌港和皎漂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孟加拉國的達卡港、斯裏蘭卡的漢班托特港與科倫坡港、肯尼亞的東非第一大港——蒙巴薩港、希臘比裏夫斯港建設中,中國參與了對象國港口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中國的海外投資市場,但在建設中也出現了若幹問題,亟待通過外交、經濟、法律等手段加以化解。尤其是港口建設投資時間長,投入成本高,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受對象國國內政治和域外大國插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大。參與海外港口建設需防範四類風險,即經濟風險、法律風險、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孫德剛,2015)。經濟風險即參與的港口建設能否盈利;法律風險即對象國在涉及港口建設、經營和收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法律限制,包括港口建設引發的環境、社會就業問題等;政治風險即對象國發生政權改組和國內外輿論變化對港口建設的影響;安全風險既包括自然災害,又包括人爲風險,如恐怖主義。
首先,爲降低風險,中國應奉行企業先行、外交保障、各部委統籌協調的原則。中資企業參與海上絲路沿線港口建設,促進了安全邊疆和利益邊疆對外延伸。中國應將參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建設作爲國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內整合交通運輸部、商務部、外交部和發改委,對外將企業利益與國家政治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外交、政治、法律和金融等綜合手段爲港口企業建設保駕護航(孫德剛,2016)。
其次,政府應合理引導參與海上絲路港口建設的中資公司。新時期,中國制造産品的“走出去”,主要有兩大名片,一是高鐵“走出去”,中鐵、中國鐵建、中國南車、中國北車等都是重要大型央企;二是港口“走出去”,中遠集團、中海集團、招商局港口、上港集團、中國港灣、中國路橋等都是參與絲綢之路沿線港口建設的重要公司。在世界前六名碼頭運營企業中(和記黃埔、招商局港口、新加坡港務集團、中遠海運港口、迪拜環球、馬士基),中國占3家,成爲名副其實的港口強國。上述港口中資企業在海上絲路沿線港口項目的開發,符合中國中長期外交和政治利益,同時須避免過度投資和重複建設,防控風險。
再次,應探索混合所有制模式。參與海外港口建設很容易被貼上“新殖民主義”、“債務帝國主義”的標簽,經當地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西方媒體渲染後,影響惡劣。中國宜邀請當地企業和其他國家港口公司入股,聯合承建和經營港口,如中資公司與李嘉誠的香港和記黃埔進行戰略合作,共同拿項目的做法值得推廣;2013年1月,招商局港口宣布將耗資4億歐元收購達飛輪船全資擁有的終端鏈接港口公司49%股份(甘琛,2015)。在走出去的同時,也要歡迎海上絲路沿線資質佳的港口公司投資中國的港口和碼頭項目,做到港口建設走出去和請進來雙向互動。例如,阿聯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在中國、東南亞和南亞共經營了20多處港口碼頭[24],成爲阿聯酋逆向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抓手。
最後,在參與海外港口建設中應實現安保公司的走出去。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和海外投資規模的擴大,保護海外利益不僅包括外交和法律手段,還包括安保手段。受限于中國防禦性外交原則,向海外派出保安是中國領事保護的重要方式。聘請專業安保公司,是確保海運安全的有效模式,不僅符合國際法,也爲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法律所允許,在夯實中國海洋總體安全上具有戰略意義(李衛海,2015)。中國宜對安保公司走出國門、參與領事保護和確保人員與投資項目安全進行管理,避免安保公司走出去過程中的無序化和盲目性。
總之,新時期中國參與海上絲路沿線的港口建設豐富了中國外交的“工具箱”,促進了外交體制與機制創新,打破了中國以往將海上絲路沿線地區劃分爲若幹片區、分別由亞洲司、歐亞司、亞非司、非洲司和歐洲司管理的條塊分割的局限性;新時期中國的港口外交是內外統籌的大外交。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交通運輸部等部委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籌下,中央與地方相互協調,政府與企業密切配合,中資港口企業與絲路沿線對象國港口企業以市場爲導向、實現優勢互補,共同致力于地區的和平與發展,豐富了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的內涵。
[1]《布局海外港口,中國在下一盤大棋》,載《南風窗》,2017年第10期,第7-8頁。
[2]《海外港口背後的中國資本:中企參與經營的有二十多個》,載《國際金融報》,2017年10月2日。
[3]“China Builds upStrategic Sea Lanes,” Washington Times,January 17, 2005.
[4]Brahma Chellaney,“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 JapanTimes, December 27, 2017.
[7]《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依海富國,以海強國》,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年8月1日,第1版。
[9]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發揮各部委統籌和協調作用。
[10]《中企多種形式參與海外港口經營,布局“一帶一路”落腳點》,載《長江日報》,2016年1月14日,第12版。
[12]此外,香港、高雄港等也是中國重要港口。
[13]中國網:“招商局:瞄准港口建設‘穴位’推廣‘蛇口模式4.0’”,http://news.china.com.cn/txt/2017-06/18/content_41049102.htm。
[14]“中國大陸港口吞吐量排名:10個3億噸港闡釋中國貿易世界第一,”
[15]《厲害了“中國港”!全球前十港口中國占七席》,載《新華每日電訊》,2017年6月20日,第5版。
[16] “The New Masters andCommanders: China’s Growing Empire of Ports Abroad is Mainly about Trade, notAggression,” 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579039-chinas-growing-empire-ports-abroad-mainly-about-trade-not-aggression-new-masters.
[17]蔣伊晉:《“一路一帶”戰略背後:中國參與了10多個海外港口項目》,載《南方都市報》,2014年11月10日。
[18] “How China Rules theWav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2017.
[19]劉俊:《“一帶一路”:港口掘金機遇》,載《中國水運報》,2015 年1月19日,第7 版。
[20]《海外港口背後的中國資本:中企參與經營的有二十多個》,載《國際金融報》,2017年10月2日。
[21]《在追求對話和發展的道路上尋找希望》,載《人民日報》,2016年01月25日,第21 版。
[22]《中企發力“海上絲路”港口投資》,載《參考消息》,2017年4月10日,第5版。
[23]王毅:“讓鐵路和港口成爲中阿交往的標志”,新華網,2016年05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5/13/c_128979169.htm。
[24] “China’s ‘Belt andRoad’ offers Middle East opportunities galore,” AMEinfo, June 19, 2017.http://ameinfo.com/money/economy/chinas-belt-road-offers-middle-east-opportunities-galore/
參考文獻:
潘玥:《中國海外高鐵“政治化”問題研究—以印尼雅萬高鐵爲例》,載《當代亞太》,2017年第5期,第107-132頁;
胡鍵:《天緣政治與北鬥外交》,載《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第3-16頁。
管清友:《一帶一路港口:中國經濟的“海上馬車夫”》,載《中國水運報》,2015年5月11日,第6版。
曹文振、畢龍翔:《中國海洋強國戰略視域下的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載《南亞研究季刊》,2016年第2期,第4頁。
趙楠、真虹、謝文卿:《關于我國港口群資源整合中實現科學整合、防止經營壟斷的建議》,載《創新中的中國:戰略、制度、文化(中國大學智庫論壇2016年年會咨詢報告集)》,中國大學智庫論壇,2016年,第287頁。
梁芳:《海上戰略通道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
Oded Eran,“China has Laid Anchor in Israel’s Ports,” StrategicAssessment, Vol. 19, No. 1, April 2016, p.53.
Vivien Fosterand Cecilia Briceño-Garmendia, eds., Africa’s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2010, pp.2-6.
蘇長和:《從關糸到共生——中國大國外交理論的文化和制度闡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期,第24頁。
甄峰等:《非洲港口經濟與城市發展》,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9頁。
王德華:《新絲路、新夢想與能源大通道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3、94頁。
IbrahimElbadawi and Samir Makdisi, eds., Democracyin the Arab World: Explaining the Defici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0.
孫德剛:《中國參與中東地區沖突治理的理論與實踐》,載《西亞非洲》,2015年第4期,第79-89頁。
複旦國務智庫編:《經世之道——探索中國大國特色經濟外交》,《國務智庫戰略報告》,2016年第6輯,第1-2頁。
趙洋:《中美制度競爭分析———以“一帶一路”爲例》,載《當代亞太》,2016年第2期,第56頁;馮並著:《“一帶一路”:全球發展的中國邏輯》,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2015年版,第2頁。
謝文卿、趙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港口發展系列之一:運輸需求與通道分析》,載《中國遠洋航務》,2016年第7期,第44頁。
劉宗義:《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我國沿海城市和港口的發展》,載《城市觀察》,2014年第6期,第7頁。
管清友:《一帶一路港口:中國經濟的“海上馬車夫”》,載《中國水運報》,2015年5月11日,第6版。
張潔:《海上通道安全與中國戰略支點的構建——兼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安全考量》,載《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7頁。
孫德剛:《論新時期中國在中東的柔性軍事存在》,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8期,第2-3頁。
杜傳志:《發揮港口綜合優勢: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支點》,載《大陸橋視野》,2016年第13期,第50頁。
Peter Hall, WouterJacobs, and Hans Koster, “Port, Corridor, Gateway and Chain: Exporting theGeography of Advanced Martime Producer Services,” in Peter Hall, Robert J.McCalla, Claude Comtois, and Brian Slack, eds., Integrating Seaports and Trade Corridor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6, p.82.
汪海:《從北部灣到中南半島和印度洋——構建中國聯系東盟和避開“馬六甲困局”的戰略通道》,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7年第9期,第50頁。
王德華:《新絲路、新夢想與能源大通道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頁。
James Jeffrey, “Chinais Building Its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 Right Next to a KeyUS One,” Global Post, May 3, 2016.
王曆榮:《印度洋與中國海上通道安全戰略》,載《南亞研究》,2009年第3期,第48頁。
孫德剛:《中國參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建設的思考》,載郭業洲主編:《“一帶一路”跨境通道建設研究報告(201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302頁。
甘琛:《戰碼頭——中資港航企業海外擴張版圖》,載《中國水運報》,2015年2月27日。
李衛海:《中國海上航運的安保模式及其法律保障—以應對21世紀海上絲路的海盜爲例》,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第131頁。